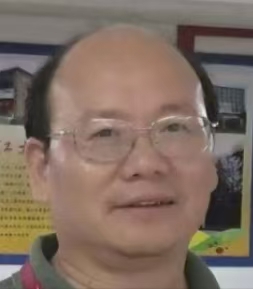在菜地除草,浇水,当我直起腰时,不远处板栗树枝头的几声“呼呼”的声音,两只鸟迅速地刺向暗蓝的夜空,火烧云渐渐暗淡,月牙儿已经挂在了空中,四周一片寂静。我仿佛又回到了在水门巷46号的日子。
黄昏的时候,我背着书包回家。夏天的傍晚,对水门巷46号来说,那是一个梦幻的世界,站在后院的小山上,眺望马街方向,夕阳在山巅依依不舍地隐没,田野渐渐地暗下去,身边一畦畦辣椒、茄子、苦瓜等蔬菜刚浇过水在夜风中挺立……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光里,我怎么也没有觉得水门巷46号的夏夜里藏着一个梦,一种幻想,我从来也不会想到,几十年后,我会一次次地回想起在水门巷46号的日子,甚至在梦中。有一些时光,只有当你远去的时候,一回头,两角的鬓毛上流下的全是这片时光里残存的苦涩。
我在夕阳下的光辉里,跨上门前条石台阶。青石台阶曾经精致打磨的边沿早已被磕碰掉,露出不规则的切面来,斑斑点点小坑布满石面,被时间用潮湿的墨汁点缀出来,上面涂满了一个一个历史的年轮,呈现出沉重的老态。那每一个小坑,都透着一种微弱的叹息。在时间的光阴里,行走的生命,都被无情地吞噬,总是短斤缺两、残缺不全。
这座原国民党上将军长周浑元的私人宅所,像历史深处的声音,仿佛默默地诉说着什么,在夏日的黄昏,像一个堆满褶皱的脸上,露出一抹蓝暗的光。
同一个屋檐下的各家各户炉灶的烟火被点燃,柴草哔剥作响,像鞭炮声一样。我像往常一样来到后院小山上的菜地浇水,莳草,幽蓝的天空下,家家户户的炊烟在夕阳里袅袅升起,飘向无边的夜空,温暖了水门巷的人家。
夜色由淡到浓地演变着。水门巷的水流哗哗地奔跑着,夏天的雨一连下了几天,罕见的雨滴在树枝上,在草叶间,然后渗到泥土里,让泥土贴实、柔软,充满生机。
虫声隐藏在菜叶子或者草丛里,我不知道它们的名字,但很喜欢听,在夜色中,你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就像这夜虫,食草饮露,只管在夏夜的梦里高亢而动听地鸣叫。
我已经多少年没有静静地听到过这样的鸣叫了?
今天,我坐在小院,用耳朵、用眼睛、用整个身体一遍一遍地搜寻着,我在手机里不停地转滑动,屏幕上闪烁的光线里,没有我希望看到的熟悉的影子!
小学时候的那个住在桥边的女同学因为母亲去世,在那个夏末秋初的时节离开了水门巷46号,嫁给了在马街深山烧炭的江苏佬,后又去了江苏。她曾经也和我们一样有过读书学习的梦,但她为了可以把母亲安葬下去,任由父亲把自己嫁了,从此我再也没有看见过她的身影。在遥远的地方,她还会想起水门巷46号吗?还听见过这样美妙的虫鸣吗?或者早已经把水门巷46号忘记,从此回水门巷46号的路上,留下的只是一路的惆怅。
曾经的夏夜之梦,被虫声一阵一阵地吵醒,现在我只能用已经有些干枯的手,还有陈旧了的思绪,在一张泛黄的纸上,记录下生命的回归夏天的第一声蝉鸣,总在水门巷46号后面的苦楝树上响起,那时候时光停留在某一年的五月或者六月的一天。我已经多少年没有听见过夏天的第一声蝉鸣了,我的心里落满了岁月的烟尘,却容不下它的一声鸣叫。
初夏的雨,在瓦檐上留下续断的叮咚声, 一滴两滴的在地面停留又消失,四周一片清新。青苔在屋檐下的石板缝里蔓生,一丛绿,一片灰白,青苔也许是时光里的雨渍,在屋檐下留下的翠色绒毛。
少年的我被那一声呜叫吸引,在屋后的绿草间,却找不到虫子的身影,也许它是来唤醒夏天的幽灵,在那一声呼喊里,我听见了夏天跑来的声音。
那里的一丛芭蕉,在阳光下,透着绿色的光;它们光滑的茎干和阔大的叶子,使水门巷46号显得清幽迷人,青灰的瓦片上,蜘蛛正在结着珠网,一滴水珠在网上似坠非坠地荡着秋千。我在菜地的橘子树上捉到一只天牛。它黑色的外壳,壳上有白色的小点,像满天散乱的星星;它身长不过四五厘米,头上的触角一节一节,延伸出去,比虫身还长了许多。我用一根白线绕在虫子的一根触角上打一个死结,然后又把另一段线迅速在捆在虫子的另一根触角上,放开摁住的手,天牛突然得了自由,振了振翅膀,然而却老是飞不起来。我拉着白线,把虫子放在桌子上,随着我每拉动一次线,虫子就顺势地低一下头,两根触角在空中划出一条弧线,然后很痛苦地“咯嵫”一声,虫子的“咯嵫”声不断,一直到残阳如血,那声音才在梦里消停了下去。
夏天的橘子树下,散着一种诱人的油浸浸的香气。它的白天,被蝉鸣渲染得热烈而畅快,那些暗红的虫子,在橘子树上飞来飞去,在清晨的阳光中,它们振了振了翅膀,发出一种清脆而激烈地叫声,阳光越是强烈,那种呜叫越显得高亢。也许正是阳光给了它们一种为生命而呜的力量,在这片土地上,最懂得珍惜生命的是那些呜叫的虫子。
……
夜已经深了,我坐在止园,听不绝的虫呜声,在这样的夜里,我等待着一种东西的归来——从水门巷46号走来,在皎洁的月色里,如一颗颗闪光的星星,只需要“呼呼”的几声,便轻快地坠在了遥远的梦里。
【编辑:晓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