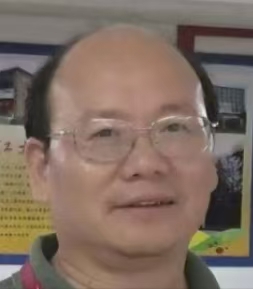当紫气东来的云霞在天际燃烧,当金乌的羽翼扫过最后一片残霞,天地间骤然腾起炽烈的光焰。这是万物生灵屏息以待的盛典——夏,携着青铜鼎般浑厚的脚步,踏碎了春的脂粉匣,将滚烫的赤足印在时光的河床。风从南方的季候带上卷来,裹挟着稻秧拔节的脆响,裹挟着荷钱浮水的清芬,裹挟着蝉蜕在树影里震颤的微芒。
我总疑心夏是上古神话里走来的火凤,每片翎羽都凝结着熔岩的温度。晨光初绽时,朝霞在东方的天幕泼洒朱砂,将云絮染作赤绡裁就的襦裙;正午时分,骄阳悬在碧落中央,恍若女娲补天时遗落的灵石,将九霄云汉都映得通透;暮色四合之际,晚霞又化作流丹的鲛绡,将西天织就漫天流火。这般炽烈,连空气都在震颤,将白昼延展成流动的金箔。
庭院里的石榴树最先读懂夏的密语。嫩绿的新叶间突然迸出团团火苗,那些花苞像被谁蘸了朱砂的笔尖,在绿绸上戳出点点朱砂痣。某夜骤雨过后,忽如千万盏琉璃灯在枝头点亮,红得惊心动魄。老茶寮的紫藤架下,青石板上落满淡紫色的蝶形花穗,细碎的清香被午后的热浪蒸腾成朦胧的纱帐。
最动人的当属荷塘盛景。晨雾未散时,田田荷叶托着露珠,像是观音净瓶倾倒的甘霖。粉荷初绽如少女含羞的笑靥,白莲亭亭似月下遗落的环佩。待到日头西斜,蜻蜓点水惊散涟漪,藕花深处传来锦鲤搅动翡翠的窸窣。记得那年盛夏,我在竹桥看见满塘红莲怒放,风起时花浪翻涌如织锦,惊得白鹭掠水而去,在苍茫暮色里划出银白的弧线。
竹简深处藏着先民与暑热的千年对弈。《周礼》记载的“凌人”官职,让凿冰贮冬成为庄重的仪式。那些深埋地窖的玄冰,承载着先人对自然的驯服智慧。唐代诗人王建曾见“玉碗盛来琥珀光”的酥山,想来是冰酪凝就的山峦,在丝竹声中化作夏日幻梦。及至张择端画《清明上河图》,汴河两岸的冰饮摊前,戴幞头的商贾正就着冰盏细品绿蚁新醅。
宋人的风雅更在竹夫人、凉簟与瓷枕间流转。苏轼在承天寺夜游时,或许正枕着荷叶边的竹席,听庭院积水映照的月影碎成银鳞。李清照的“红藕香残玉簟秋”,倒教人想起她午倦抛书时,竹席沁出的沁凉如何漫过罗裳。最妙是杨万里笔下“冰碗生花”的妙趣,官窑青瓷盛着冰雪冷元子,恰似将整个荷塘的清凉都凝作方寸之间的琼瑶。
暮色四合时,整个天地化作巨大的音箱。蝉鸣自梧桐深处涌来,先是试探般的独唱,渐渐汇成排山倒海的合奏。黑蚱蝉的清越穿透力能震落槐花,蟪蛄的低吟则似揉皱的生宣。那天,柳永听雨,忽觉雨打芭蕉竟与檐角铁马声暗合宫商,瓦甍漏雨如琵琶急弦,竟谱成天然《雨霖铃》。
最惊艳是骤雨初歇的刹那。乌云裂帛处漏下鎏金般的光柱,积水洼里倒映着洗练过的碧空。青蛙们从荷叶下跃出,在涟漪间敲响玉磬,此起彼伏的蛙鼓应和着远处的蝉琴,竟教人想起敦煌壁画里飞天反弹的箜篌。山泉穿石成帘,泠泠水声与松涛和鸣,恍惚听得七弦琴上滚落的冰霰。
文人的笔锋总在盛夏最浓处蘸取灵感。李清照的“误入藕花深处”,让整个宋词都染上荷香。赵师秀“闲敲棋子落灯花”的闲适,却不知窗外正有流萤提着灯笼,在瓜棚豆架间书写光的诗行。最动人的是张岱湖心亭看雪的余韵,却不知他写夏夜泛舟秦淮时,笔底烟波更显旖旎。
夏九九歌谣里藏着农耕文明的密码。“一九至二九,扇子不离手”,老农的棕叶扇摇落满地星河;“三九二十七,冰水甜如蜜”,江南闺秀的琉璃盏中浮着碎玉般的甜意。这些散落在民间的歌谣,恰似散落的珠贝,串起中国人独特的节气美学。
晒谷场上的稻子在热浪中翻涌,金黄的波涛里沉淀着农人的汗水。蝉蜕仍挂在苦楝树上,空壳里封存着蜕变的记忆。瓜藤攀着竹架编织绿色的迷宫,葫芦在阴影里酝酿清凉的童话。连石缝间的野草都攒着劲儿生长,将根系扎进滚烫的岩层,把绿意写入滚烫的夏天。
最动人的生命图景出现在某个骤雨初晴的黄昏。蜗牛沿着湿漉漉的紫藤攀爬,在叶片上画出银亮的诗行。蚯蚓拱破板结的菜畦,翻起的泥土蒸腾着腐殖质的芬芳。断墙边的凌霄花突然绽放,橙红的花朵像燃烧的火把,将整个夏天的激情凝固成永恒的瞬间。
当季风开始转向,当银河在夏夜里愈发清亮,我总想起敦煌壁画里的飞天。夏天何尝不是这样惊心动魄的艺术?它用雷暴作鼓点,用蝉鸣谱旋律,将滚烫的激情倾注在每寸土地。那些在树荫下打盹的时光,那些冰镇酸梅汤里浮沉的薄荷叶,那些突然掠过天际的流萤,都是夏天写给岁月的情书。
此刻站在紫藤花架下,看暮色将白昼的锋芒渐渐柔化。晚风送来荷塘深处的暗香,混合着井水浇石的清凉。忽然懂得夏天为何要如此炽烈——唯有以这般决绝的姿态,方能在时光长卷里烙下永恒的印记。那些被晒暖的陶罐,那些被蝉鸣浸透的黄昏,那些在树影里婆娑的碎金,都在等待某个霜降时节,化作记忆里温润的琥珀。
当最后一缕霞光沉入西山,满天星斗忽然亮起来。夏天并未离去,它只是换上素绸的衣裳,将炽热藏进蝉蜕的空壳,把热烈凝成葡萄藤下的阴影。我们终将在某个起雾的清晨发现,那些惊心动魄的炽烈,早已化作陶瓮里窖藏的月光,在岁月深处静静发酵,成为生命里最醇厚的回甘。
【编辑:南栀北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