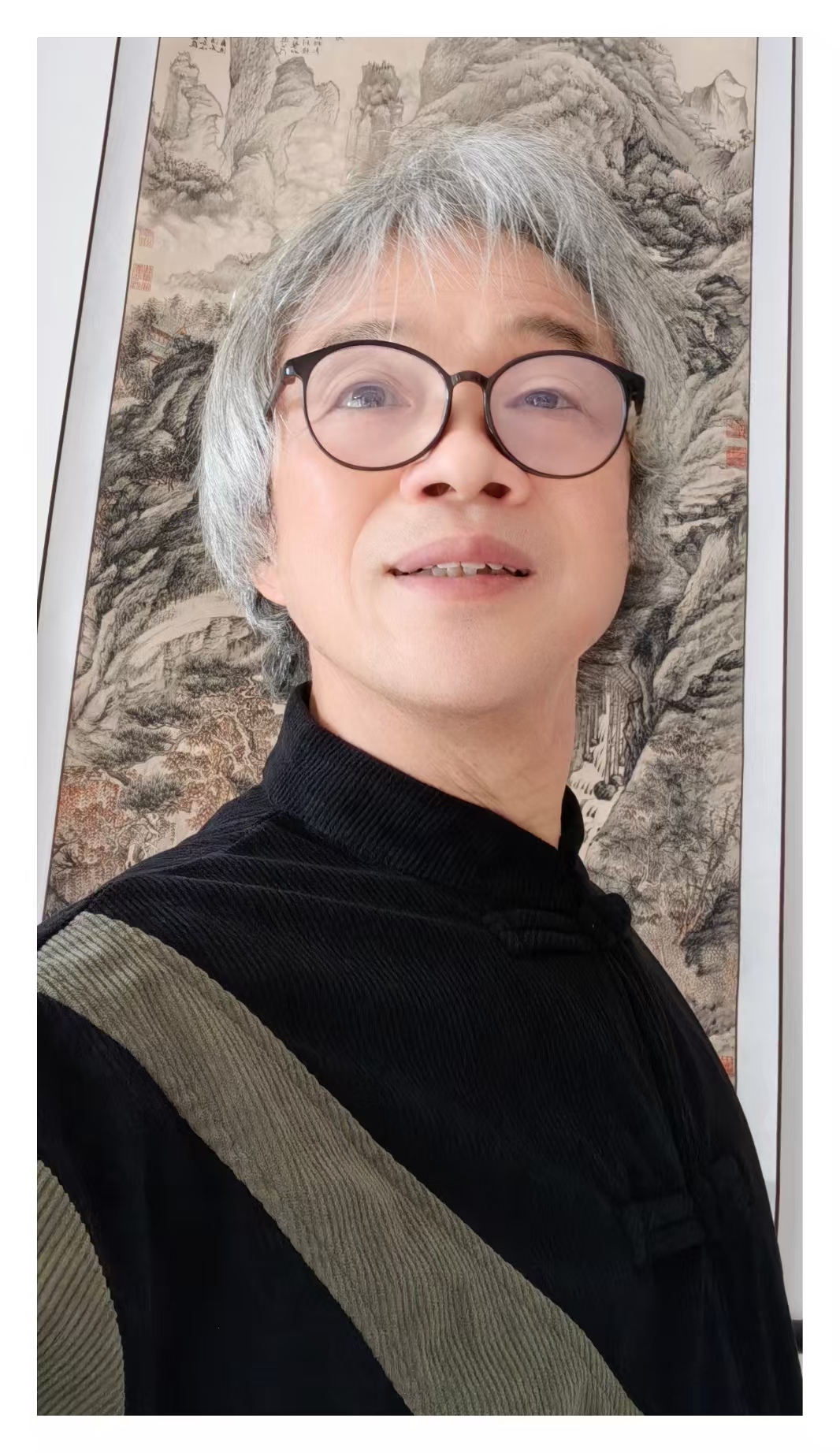泥砖屋,是最好的屋。
那是说,泥砖是最好的砖。
这话不是我说的,站在故乡有祖坟茔的山坡上,世世代代的先祖把心声托付给天空的风和飞鸟,风声、鸟声如是说。
中国最早的土坯砖(未经烧制)可追溯至4000-45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这类砖以黏土为原料,通过模具成型或手工摔打制成方正土块,用于砌筑墙体。大约出现土坯砖后很快就有人动了烧制成陶的心思,只要成了陶,那就万年不腐,今日鄱阳湖北岸的陶片,多数是新石器时代和西汉残留的,几千、上万年的雨水、湖水冲刷,对那些陶片的改变很小。火砖就是一种陶,鄡阳古城区很多汉墓砖几无形状和性质的改变,被风雨、湖水侵蚀的城墙砖至今硬度良好,轻敲即有金属音。
就是说,人类最早烧制的砖至今没有被降解掉,还是以垃圾的形式存在的,被这种垃圾占位的地方,植物是无法生长的。
鄱阳湖区古饶州地面著名的瓦屑坝,就是因为那里有太多的瓦砾得名,得名可能在明朝,瓦砾却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都昌地面也有“瓦碎坝”,其“瓦碎”也是同种性质的远古留下来的垃圾。
现代水泥构件的寿命是五十年,好似很短,但这只是从房子保质的要求判定的,水泥构件的完全降解需要几百上千年。很难想象,大地上不断更迭不断增加的水泥费件在数百年后会形成多少的“瓦砾”,人只怕挤得无处容身无耕作之土。
这么说,不经烧制的土坯砖才是唯一不会给大地带来伤害的建筑材料。
那当然是。
泥胚砖一旦被废弃,很快就会回归成宜于耕作的泥土。
但最初土坯砖的形成,也是对环境进行过直接破坏的。
我所知绝大多数的土坯砖,是用稻田的泥土制作的。
我目睹了母亲为制作土坯砖而辛苦劳作的过程。
我家八九个人,只住五树三间屋子的一半,容身之难至极。晚稻收割之后,母亲反复向队长申请打制一千块泥砖,得到批准。正是稻田里的土不干不湿之时,母亲每天天不亮就到三角田里去劳作。
用砖槌(用打麦的櫣杖改装,把竹板换成厚实的木槌)反复规则地拍打地面,日复一日不间断。那是男子干也很累的活,得尽力把砖槌高举过人头,狠狠地拍打,没有使用过櫣杖的人根本抡不转,即如学会了,不几下气力就消耗得不能维持下去。哎呀,真不知母亲瘦弱的身怎么坚持下去的。大约半个月后,师傅察看后认可,就约定好切砖的日子。父亲、母亲像拉犁一样拉,师傅在后面把握切刀的位置和方向。当然是拉的人吃累,师傅吃力的时候是切好砖后将砖端起摆放到一边,时间久了,自然也不轻松。
切砖的过程很让人觉得解压。整齐的划线,似干还湿的泥土,拉切刀的人用力很规律,等值的时间里,出预期的砖,切刀闪着好看的寒光,悄无声息地切入泥土,让人感受滋润和力量和希望。一块块整齐的新砖码放整齐,每层六七块砖的高度,形成一道好看的散发着芬芳的湿墙,砖里偶然会显出可生食的植物根茎,有时还有一开始冬眠的泥鳅甚至小黄鳝,孩童见了会鲜花怒发。
夜,月亮升上了来,砖田有了别样风景,一堵堵排列整齐的黑墙,像让人想起童话里的古堡。里面该有老妖婆,有受伤了的狐妖,有住在森林里的外婆,有狼,有斑鸠咕咕咕……也有骑马射箭的王子、侠客。砖堂成了孩童玩耍的天堂。每一个孩童都想到里面当一回侠客,在砖堂里神游到夜半,月亮疲倦地打起哈欠,孩童才陆续悄悄钻到自己那个虱子等急了的家机布被窝里去。记得那次我站在梦中城堡上很不爽利地拉尿,被母亲唤醒,要我去挑砖。就是把砖堂里的砖挑回家来码放。一头一块,一块砖约二十斤,那就是四十多斤的担子,挑是挑得起,人家说我“打西风戗”(趔趄)。我尽量控制自己的步伐,想不被人家诟病,但是做不到,气得我把一泡尿狠狠撒在一块砖角上露出的田螺上。田螺被“大雨”促得透不过气来,最终透过气来也不敢言语。哈,活该!我和母亲每一趟可以挑八块砖,看着那一千多块砖,我头皮麻麻,鼻涕乱流。
一般人家要几次制砖(一年只能一次)才能积累到足够一幢五树三间房屋的用砖。我家那时极端贫苦,造屋的希望非常渺茫。母亲盘桓再三还是实施了制砖计划,也只是申请了一千块,做厦屋的砖也不够。母亲大约是想把父亲“逼上梁山”。到底父亲还是没有能力积攒造屋的钱。父母一辈子没有造屋,但真制过砖,那些砖曾经堆放在老屋的厅堂,母亲和三娘关系不好的时候,泥砖做过两家房屋使用分界线,土砖的再一个用途是做过冬取暖的火塘。
其实那砖的成本很高,人力不算,师傅按两分钱一块得工资。还有一个隐形的成本是未来稻田的明显减产。拍实了尚有四、五寸厚的砖块,基本耗尽了稻田里可用水稻生长的泥土,剩下的是贫瘠的沙质壤。如是放弃不管,那就成死田,来年勉强再种水稻那必然是不出产量的。
农民的挽救措施是冬季补充塘泥。干涸的水塘里有大量的淤泥,这个肥料还是很不错的。农民及时把塘泥挑到需要改良土壤的地方。塘泥会作为肥料分到很多旱地去,切过砖的稻田虽然会得到较多的补充,比起因切砖造成土壤的损伤还是杯水车薪。一次切砖,好几年稻田的肥力都缓不过气来。
也有利用不能耕种的湖滩制砖的,湖滩泥层薄,土质黏性差,制作的砖质量也就差多了。我所见周溪虬门利家村有那样的屋子,砖墙呈酸壤红,墙体歪歪扭扭,被雨水打得百孔千疮,随时要倒塌的样子。
我可以想见,千百年来,我的先祖就是和我父亲母亲一样的做过制砖造屋的梦,可能一辈子都在梦里纠结,运气好的先祖,可能梦想成真,千辛万苦制了砖,又造了屋,那就有了非常好的人间烟火。也有先祖沦落到没有土地的地步,靠给财主做雇工活命。财主是绝不会把土地让给人制砖的,也不会用自己的土地制作砖来出售。所以没有土地的先祖就不念造屋的经,只能做做买田置地的美梦。也有先祖有了些土地,不舍得用“肉土”制砖,或是有的先祖如我的父母,虽然有幸制了些砖,却始终没有能力买瓦或做栋树、桁、椽的木材,那就可能是用泥砖围个漏风雨的厦或是茅房。
走在欧洲的大地上,看到欧洲的农村没有高楼大厦,只有零星分布的平房,几无砖墙。欧洲的土质非常好,土地广袤,人说是“上帝偏爱的地方”;但欧洲人却那么抠门,不用泥土制砖,更不会烧砖成“陶”,他们肥沃土地上长出的木材造屋,一幢小屋会用很多年,乃至代代相传,足够被砍伐的地方长出伟岸的树木。
我的先祖不是不会用木材造屋,鄱阳湖区千百年来没有大的森林面积。往东北到婺源、浮梁,森林资源丰富,那当然用木头做墙体是自然的事。
木头做墙体是有欠缺的,防火、防虫、防腐蚀性能相比要差得多。所以浮梁山里富有的人家也是会造泥胚墙的,山里缺少稻田,不会用稻田的泥土制砖,会寻找不能种庄稼的酸性黏土,进一步烧制成砖,墙体内的结构还是用木材,这当然是很高档的房里了。
因为土壤资源的有限性,古代只有官家或少数富豪才可以用厚实的陶砖造屋造城墙。民间有钱人家造棋盘屋也只是用“烽火砖”,那砖厚度只有约1公分,长近一尺,宽约八寸,单砖围起的“万字斗”里填入山土。“烽火墙”最大的缺陷是不抗外力破坏,孩童用鹅卵石也可以轻易敲破墙体,“万字斗”里的土随之溃出。敲破的墙体很难修补。
民间常有人从墙缝里找到珍宝的传说,那绝对不是“烽火墙”,烽火墙没有缝,一旦有破洞也不适宜藏物。有藏物的就该是泥坯墙。泥胚墙厚实,沾砌用泥也粗厚,这泥没有经过夯实,容易被外力所破坏。时间久了的墙体难免“百孔千疮”,旧时百姓人家,确实把小件物品藏于内墙的这些隐秘的“洞穴”。十年前,我在岳父的姐姐家最后一次看到这种给人神秘感和亲切感的墙体。一张旧式床靠着泥墙放,墙体有很多年代性的改变,让人猜测很多种种令人感受温暖的故事,墙缝很大,但只有少数穿孔,一个一个高地错落的不穿孔的墙缝里塞着主人存放的被其认为不能丢失的东西,比如户口本,比如购布证、社股证,比如一角一元攒起的新旧不一的货币。
鄱阳湖区“鄡阳遗址”乃至更大面积湖区的“瓦屑”,有残存的城墙砖,没有“烽火砖”,也没有瓦片,所谓“瓦屑”,其实是器皿陶片。甚至西汉时期的“筒瓦”片也极少见。那里残存的陶片绝大多数来自新石器时代,那时人会凿洞为屋,也会用树木搭建棚屋,不会烧陶砖建屋。鄡阳城是西汉时期始建,到南北朝瓦解,城墙、官屋用厚实的陶砖建造,民间只有泥胚房,不会有陶砖墙。鄱阳湖形成后那些地方至今没有人居住。“瓦屑坝”无瓦无砖是正常的现象。
瓦屑可以万年如昨,水泥构件也可以萎靡百年,泥砖只要不被严重的水侵蚀,那是可以永恒的。
生命,理论上可以永恒,个体寿命却非常有限,泥砖和生命的个体相联,所以泥砖是不会永恒的,化作泥土才可以和地球同生命周期。
生,就意味着死。土坯砖是模拟的生命,活者说是生命的衍生木,会因为某个或某些生命的存在而诞生,也会因为某个或某些相关联生命的灭失而消失。这种灭失没有勉强性质,所以是自然的。
这有些像树上的鸟窝,鸟窝的性质是树枝、草或泥土,树枝和草都会归于尘土。如是构件是塑料(如今已多见),那就有些错乱,小的错乱可以恢复,但小的错乱会积累成大的错乱,大的错乱则会引起上帝构建的函数左右不等,消灭活着的和可能活着的人文。
这种东西,最应当被视为人间之丑。
我只能算一个丑人,但我梦见昨日泥屋。
【编辑:晓晓】